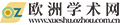同学聚会,因一张网红照片而热议是事先不曾预料的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沃特·阿鲁法特是二战期间的一名美国海军士兵,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,因为随军执行任务,在上海停留了5个月。在此期间,喜欢摄影的阿鲁法特拍摄了不少反映上海市井风貌的照片,其中一张题为《吃蟹》的照片近年来风靡了朋友圈,每到蟹秋,这张“上海人狂吃大闸蟹”的老照片总会疯传。它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。讨论的焦点是:那年头的上海市民真的有这么好的“口福”?
那天,网上的争论居然延伸到了同学聚会。一女生称当年大闸蟹不但不稀奇,而且还是“当地一害”!四十年前她在安徽巢湖某地做过小学老师,当地大闸蟹不但贱得没人吃,而且大面积地毁坏水稻,屡屡造成减产,县委号召广大基干民兵,发动群众,“除蟹害,保丰收”,为此很多青年推迟了“国庆婚礼”而投入“战斗”,我们那女同学也动员了所有的小学生,利用大闸蟹的趋光性,在稻田四周拉起渔网,点起火把,通宵杀灭。
以后的日子,当地农民把她尊为“女强人”,因为她“敢吃蟹”,而且顿顿吃,没成想大闸蟹是万万不能“当饭吃”的,她连吃了一个多星期,不但例假乱了套,而且腹如刀绞,头晕目眩,从此落下了例假期间偏头痛的顽疾……
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她的“信口开河”而目瞪口呆。看女生尴尬,我说,我当年下放的地方也是安徽。“宁国县”。附近是著名的水网地区——宣城,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,上海职工刚去“小三线”的时候,皖南地区也是不吃蟹的。蟹也有大年与小年,大年的时候,无数的大闸蟹会集群迁徙,卡车在土路开过,轮下顿成一望无际的厚厚的“蟹糊之路”,老乡们居然用铁锹铲起喂鸡鸭鹅猪。
一同学听了大发感慨:明明珍馐,不知珍馐,即是信息茧房;知其价值而无法流通,即为“价值茧房”,一旦进入,立马死翘。
所谓“吾之蜜糖,彼之砒霜”,东北的农垦大军最先见到的场景不也是“棒打狍子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锅里”吗?苏东坡当年被贬黄州(今湖北黄冈地区),也为当地猪肉“贱如泥”吃惊——“富人不吃,穷人不懂”,盖因猪肉腥膻,当地人不懂“多加酒,少放水,小火炖久成美味”的道理,便满大街的万人嫌。
“想听听我的故事吗?”旁桌一直听着我们的热议而保持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口了。年近八十的他,脸上的沟壑密密如麻。他说,我是当年的上海赴疆知青,因为常年放羊而练成了一手绝技:扔石头。《水浒传》里面有个“没羽箭张清”是吧,一块鹅卵石,想打你鼻子,不会打到眼睛。你们信不信,我的本事绝对不亚于他。那是放羊练的,天天打,用满沟的烂石头代替羊鞭,当地的老牧人是我的师父,他做个“面靶”戴着,天天训练我,面靶上画着五官,他手执羊鞭,要我打他脸,打错位置,“嗖”的一声,他的皮鞭就抽过来,百发百中,我越打越神,他也越站越远,直到有一天,我能精准地打到50米甚至百米之外,远远的头羊,我一块烂石头就能左右它的方向。
我们的放羊地就是和田地区的皮山县附近的塔里木河畔,那里的古河道水源不稳定,时而湿润时而干涸,我们也就跟着水草漫游,除了肩背帐篷,我们的腰上永远悬着一个大皮袋,里面鼓鼓的永远装满着塔里木河的烂石头,打羊,后来干脆练成皮弓打鸟,和我师父烤着吃。
多年后,我回了上海,有一天突然发疯似地用头撞墙:那满大街卖疯玩疯的“和田玉籽料”,不就是当年我们扔羊打鸟的“烂石头”嘛?!什么“糖皮”,什么“羊脂玉”,我敢打赌我当年扔出去的每一块都是!我直奔当年的牧羊地,但师父早死了。我们的放羊地——偌大的古河道早成了“矿山禁区”。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了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作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
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(胡展奋)